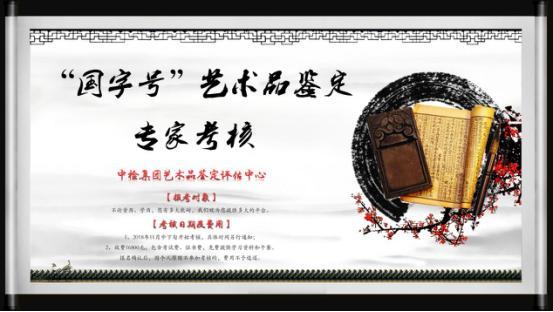墨韻才氣干云宵 書藝當從苦中來 ——齊人王登武書法賞讀感言
墨韻才氣干云宵 書藝當從苦中來
——齊人王登武書法賞讀,感言
文/張振義
1月16日,“王登武書法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展,展覽展出了來自中央電視臺的書法家王登武50件精品力作。北京翰墨拍賣有限公司拍賣了他書寫的《古詩集錦》書法長卷作品,成交價29.5萬元。

齊人王登武在畫展上(左)
王登武的書法作品,墨韻豪氣干云,神意磅礴千鈞。在當今中國書壇上獨樹一幟。匆忙采訪中,王登武先生對于他的書法藝術近四十年的行進過程,笑言道:書法藝術之路,漫長而艱辛,人磨墨,墨磨人,只有鍥而不舍,矢志不移,耐得寂寞,吃的苦頭的書癡,在經年不輟的追求和領悟中才能夠收獲“一星半點”的書法成就。
王登武先生筆下的書法幾乎涵蓋中國書法“行草隸篆”的所有形式,尤以行、草造詣頗深。行書,是當今書法實踐者最喜愛最慣常的一種書體。王登武將“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生活的那個年代前后的所有大家幾種最具代表性的書法風格加以綜合精研吸收,融會貫通之后,在深層理解,傳承嫁接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全新面目書法藝術風格。你若在他的行書中看到一種犀利的筆鋒、錯落的造型、擺動的章法,虛實的運用,節奏的跳躍,筆法的精巧組合,那便是他融合了漢魏晉唐時期眾多大家經典書法藝術元素精心創作整合的結果。這種綜合傳承,一方面使得王登武的書法藝術贏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到書法藝術“新創”的某種神韻與效果,我們可以從中領悟到書法所特有的美學快感以及由之帶來的藝術視覺視覺的震撼力。
如果說在王登武的行書中,你不難領悟古代文人士大夫創造的經典書風的痕跡,而在他的行草中,那種書法根源生命力便赫然明顯的令人感動。面對他筆下這樣的作品,我們首先想到的便是有傳承的厚積薄發。的確,書法是具有審美和文學難度的一種獨特國粹藝術,由晉唐文人創立的無可逾越的書法豐碑,把許多人擋在了林林總總形形色色的關隘谷底,難以走出迷茫,許多書者一生傾力筆墨,乃至耗盡全部人生精力,最終都前功盡棄地沒有掙脫書法技巧的桎梏和羈絆,或因才力不濟流于粗淺,或因獲叛經離道迷失方向而墮入低俗。書法歷來就不僅僅是一種書法樣式或風格的修飾和臨摹,它已是一種精神或人格風范的藝術再現,書者需要學識的集蘊和人品的高貴。王登武先生大約受到先天的厚賜和深厚家學的熏染,所以他平日的筆墨實踐盡管不屑于在古人的身后亦步亦趨,但他認同古人創立的某些用筆、結字法則,并且能夠對書法的真諦加以心領神會。于是,我們在他的筆下,看到的不再是那么方折殺伐、左沖右突,拘泥不前的模仿,那種圓融飽滿、端莊勻整,靈動深邃的筆墨變化組合,看他的運筆行書,完全是出神入化的龍飛鳳舞,激情奔涌。從技法上講,作者將用筆的起承轉合,行云流水,章法的跳躍奔放,筆鋒的千變萬化,結構的放蕩不羈,用墨的俯仰錯落,濃淡相宜。幾近完美,一氣呵成,都足見作者的書法功力,以及才情的汩汩涌動,作品躍然紙上的方寸之間,卻有著凝蘊高遠的大天地,這是完全脫離了低俗的表現,而且更多思想高度深邃沉重滲透在作品意境的深處而不是直白的露于表面。

齊人王登武在韓國景福宮文化訪問
王登武先生的書法歷練,一定不是嘩眾取寵的那種自我造作,他的筆下功力絕不是淺嘗輒止的“花拳繡腿”,我們在他的作品中能讀到作者的國學集存和厚重藝術修為。在他的頗具造詣的作品面前,他不無謙遜。他說:書法是我們民族特有的精神秘符典粹,他的神圣與天地同存,與日月同輝。書者不過是中國文字的虔誠教徒。每每用墨,都是對我們民族精神的虔心朝拜。我們可以從書法中獲得滋養精神的靈感,但是書藝不可能極盡完美,書法博大精深,永無止境,古往今來,再大的書家,都不可能也不能夠攀上書法的頂巔!
王登武對于書法的理解和常人有所不同,這是他的書藝和低俗完全背道而馳一個旗幟。談到他的書法成就,他說:“對于書法,我永遠都是一個小學生。我一直不覺得有誰可以成為書法大師,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古人不能,現在人也不能,后來者也不能。相對來說,寫的好一些,有一些造詣,就很不錯了。書法是極有高度的藝術,和其他藝術不同,不可同日而語。”

齊人王登武在戊戌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
談到他近四十年的書法感悟,他說“我大約在四歲就開始練習書法了,練了幾十年。書帖用了很多,大約常不離手浸淫多年的有幾百本,三國兩晉南北朝以來的書家,凡是能夠找到的,我都一一拜謁過,算來也有四五百人,他們都是大師,我甘愿拜倒在他們門下,幾乎每天都要盡心臨他們不朽作品,數十年如一日,從未間斷過,對于書法的癡迷,以致到了沉湎不移的地步。他們是宗師,我受益于他們的指引。我沒有才能,像有些書者,能夠無師自通,不需要傳承而自己獨創書法。我堅持了幾十年,感悟有一點。”齊人先生自嘲自己的學書過程一是——學不專一。他不像有人一生只學四大名家,他除了四大名家,還學了和四大名家齊名的百家,到了中學時期,他的書法就已經在當地小有名氣了。二是見異思遷。在練習書法的大學時期,他總是這山望著那山高,凡是覺得具有審美價值的書帖,總是要精心鉆研。三是狂放不羈,無拘無束。用筆方法,行筆技法,在遵循古訓的基礎上,率直任性,絕不墨守成規,循規蹈矩。他那個階段,自己總結了十八首書法秘訣,不斷地領悟古人,獨獨出心裁。四是好高騖遠,追求完美。在齊人先生看來,學習書法最重要的是審美,就像學習音律需識簡譜。首先知道什么書法是美的,美在哪里,怎么寫才美。追求美就必須心存高遠。他的感悟雖然是自我調侃,但細細琢磨,也頗有道理。

齊人王登武在畫展上與美國前副總統法律顧問哈維先生
草書,或說融合了所有書法形式的自由書體,也是書法蘊聚精粹的書寫形式,大約是最具王登武個性特色的書法樣式。當他在創作此種樣式時,最富情緒,最為自由。可以說,王登武平時對藝術與創新的理解,對書法這門古老藝術的把握、對它的摯愛,都傾注其中。所以,在他草書作品中,此類樣式最為被藏家青睞。
一如齊人先生其他風格的書法,在他的行草作品中,我們看不到明顯的取法
齊人王登武在臺灣藝術交流
是閃耀著創新的光輝,我們都無法得知他的“異想天開”是從哪得取靈感,但凝神揣摩,每個作品每個字又無不靈動高古,神韻迭出,投射出書法神奇靈感的魅力:用筆圓潤,硬直、剛狠,多變,靈動華美,大氣凝重,結構聚散反差明顯,注重墨骨張力……
不止于此,除了行草狂草,他又將諸如魏晉時書風拙樸的碑版或摩崖石刻的一些性格元素融入其中,以對比、反差、失衡等等手段來強化作品的效果,以期達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藝術效果。這一點王登武先生更具匠心,不能不令人欽服。

齊人王登武在中國美術家網絡電視臺邀請展上
現代美學曾有一個“陌生化”原則,意即藝術家應該善于利用現存的或新創的手段,為作品制造一種新奇的形式效果,從而使“創作”不再是“輕車熟路”,“作品”也不再是“似曾相識”,一切被“陌生化”了,它對觀者產生出一種新異的刺激,一種新的審美欲望或沖動便由此被激發出來。正是由于此種原因,那些看去并不通俗,甚至較為怪異的藝術形式或樣式,有不少時候,比起通俗的形態更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




齊人書法欣賞
書法的墨線雖是從王登武先生的筆底淌出,但它們卻往往縈繞在讀者的心頭。為了更好地抒寫心中的這份珍愛與虔誠,他不僅向古代的碑帖、向逝世千百年的先人學習,還踏遍神州,尋訪名師,聆聽教誨。在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潛心實踐中,他漸漸心手相應,心緒源源不斷地從毫端流淌而出。不求精致、不求華美,只憑一份拙樸、一份真率,便將一個文人書者的豪情與摯愛揮灑而就。或許,他還有遺憾,還有曲折,還有種種言不達意的困惑,但書法是他顯現自我,表達自己對人生、社會、自然看法的最為純真的手段和形式。他因此而憂、因此而樂,他的生命也因此而充實、而豐富、而強健……
(本文載入《藝術視點》第七期)
本文作者:張振義 (新華社原歐州記者站站長,現為文化部書畫藝術鑒定委員會特聘專家,圓明園文化專家等)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