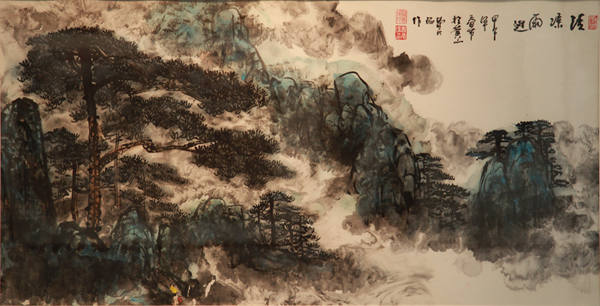王冠:霍克尼先生與迪奧小姐的歷史遺留問題
大衛·霍克尼在中國最新出版的“談話錄”,在“春至”展中供觀眾翻閱。
如果藝術史就此終結,那就是文明的終點。讓你感到“不安”的藝術,成了不再有別于權力、金錢、世俗虛榮下的庸俗玩意兒,淪落為不需要特別的感受能力就能領略到的安全的俗常審美。于是,不得不去思考以往人類發展中藝術的“高度”“深度”“廣度”將在未來被安于何處的問題。
它是被徹底自我覺醒后的人類文明所不需要再加以探求了嗎?它是已進入到從大眾生活、商品交易中就能被創造的全新時期了嗎?
藝術終結,消融進入大眾,有點相似于“共產主義”的理想——沒有了階級,按需分配,終極幸福。“共產主義”的實現需要終極完善的制度(法)與終極圓滿的人性(心)。但只要矛盾與進化仍舊存在,它就只是烏托邦的理想。因而,當時代中的人類精神活動還在因無常的變化產生出新鮮的感受與問題,大眾生活仍有墮落與平庸的危險,而商業原則下的“銷售——滿足”式的服務性創造不能填滿人類追尋自由的全部野心,那么“藝術”活動就不會消亡于日常領域之中,就還會有特殊之“人”與“圈子”將其擔負起來。
觀眾在閱讀“迪奧小姐”的文獻資料
觀眾不會自覺的喜愛杜尚與沃霍爾。觀眾的不喜歡并非源于“看不懂”的不喜歡,是竟然帶著一絲懷疑而“看懂”了。觀看藝術的期待之心,天然包含著“技術上做不到的‘懂’”(古典及現代唯美油畫)和“技術上能做到的‘不懂’”(看似輕易模仿的抽象繪畫)。比觀看那種糊涂亂摸的抽象表現主義作品更惱人的,是“小便器”“鐵锨”等日常用具與“湯罐頭”“瑪麗蓮·夢露”等隨處可見的廣告圖片出現在大都會博物館、蘇富比拍賣會中,一種幾乎沒有技術性且隨處可見的工業產品、商業美圖竟然成了名利雙收的偉大“藝術”?達達和波普,因其雙重意義上的無聊,侮辱了觀眾在感知上的“求知欲”,藝術失去了它應有的內涵。這時,觀眾心中再次泛起的“不懂”,上升至藝術的基本道理,而非具體的作品本身。
藝術家為“迪奧小姐”展覽創作的裝置作品
“我恨抽象表現主義!我恨它!”安迪·沃霍爾認為,“我是一位大眾的溝通者,普通人才喜歡我的畫。”作為一名最初的商業美術家,他試圖解救觀眾于抽象表現主義的精英牢籠,卻又將觀眾從對藝術的期待中帶入到另一個更深的牢籠。由此,理解波普藝術,必須要將它完全還原至那個時代語境之中,觀眾得到的并非一個可以反復把玩的視覺結果,而是一個考量時代的“佐證”,再反過頭來贊嘆這個“佐證”的來之不易的智慧。漢密爾頓、沃霍爾、利希滕斯坦等人的波普智慧中包含著這些方面:①與一般時尚、廣告、漫畫無甚大異的形式;②不及真正流行文化如好萊塢大片、迪斯尼樂園、綜藝娛樂節目的激情;③以圖像重復、簡單拼貼、照搬漫畫等方式在精英藝術中搶先注冊“視覺商標”從而高度概括所處時代的氣質;④“每個人出名十五分鐘”對現代人空虛、貪婪之人性的赤裸裸的揭發......波普藝術的失敗同樣表征著時代的失敗,快速消費的蒼白精神之下使藝術喪失了古典主義與早期現代主義的經典性,這使后來者在離開時代語境直觀沃霍爾的廣告圖片般的作品時必然生出一股令人厭惡的無聊感,與觀看拉斐爾、梵高、畢加索形成鮮明對比!
觀眾與“迪奧小姐”展覽中的作品進行互動
小女孩身處“迪奧小姐”的“鏡子”作品中仰望天空
沃霍爾的藝術借用商業美術的工具,簡單轉化(重復)后觸及所處時代的核心問題,杜尚則借用平常的“心境”直指現代主義中的精英困境。仿佛飲鴆止渴,又是草木皆兵,一招制敵而不拘泥姿勢的好看與否。后沃霍爾的藝術時代,被他打開了一扇通俗易懂的商業之窗,但并非如其所言可以無畏到“生意就是藝術”的程度;后杜尚的藝術時代,被他推開了一扇生活物品的裝置之門,但藝術家們并非真的集體過起了“呼吸就是藝術”的平凡日子。藝術家的話都是對著精英藝術史說的——沃霍爾曾努力擺脫商業畫家的身份——藝術史是對著時代與人心的變化說的,由此聯動起人類文明。他們以精英的心靈偽裝起大眾的立場后再反對精英的身份,試圖開辟新格局。類似于毛澤東發動紅小兵打倒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將手中的牌重新洗了一遍——但洗過之后,只要人類歷史沒有完結,就還會有新的精英出現在新的平臺與游戲之中——“藝術”在這里成了一個動詞,一種手段,而非一個精致的名詞和一個完美的結果。杜尚與沃霍爾都做到了,而他們后來的諸多門徒卻在誤解中,在粗陋的“買賣藝術”“冒充隱士”的宣揚中分別模仿、誤讀、背叛了他們的祖師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