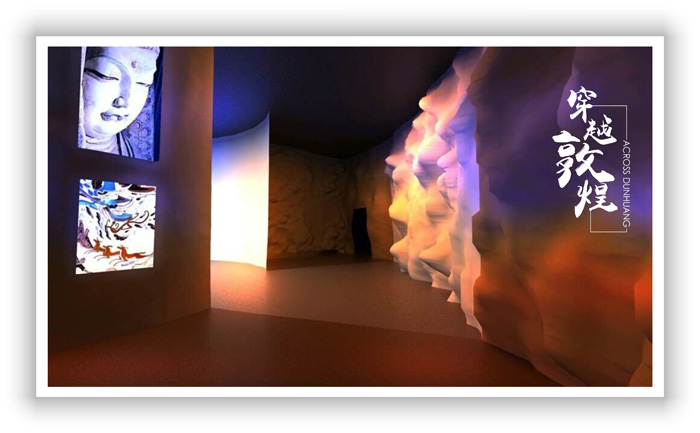沈也:傳統文化媒材的當下視覺創造
2015年3月7日,由皮道堅、陳彥翀策展的“漆語·三人行”在廣州33藝術中心開幕,展覽展出了張溫帙、沈也、謝震三位當代漆藝家的漆藝作品,跟“精神還鄉者”張溫帙中西結合的漆藝現代性的建構和解構、謝震向楚漢儀式化古典生活致敬的漆藝探索不同,當代藝術家沈也身上“漆藝”的標簽最模糊,他只是自己的當代藝術裝置作品中使用了大漆這一媒材。因為拋棄了工藝的桎梏,不管對于大漆這種東方性材料,還是對于廣州的觀眾,沈也的作品具有非常強的顛覆性。作為非漆畫專業背景的藝術家,為什么會選擇漆這種材料?大漆最吸引他的是什么?讓漆這一傳統媒材從器皿制作工藝中溢出成為當代觀念表達的語言方式中的難點是什么?雅昌藝術網記者現場專訪了藝術家沈也。

藝術家沈也
雅昌藝術網:作為一位非漆畫專業背景的藝術家,您為什么會選擇漆這種材料?
沈也:我是福州人,對于大漆這種材料從小就不陌生。這幾年來,我開始越來越多地使用大漆這種材料, 在用漆材料前是做了很多的“排除法”,大漆跟其它的諸多材料做了比較,最后得出一個結論:大漆最吸引我的是漆的"精神"。這是其它的材料所無法代替的,它就是東方所特有的材料,這是我選擇大漆的理由。
雅昌藝術網:除了精神上的意義,漆還有什么特性吸引了您?因為對于當代藝術的創作,能用的材料非常多。
沈也:首先我是一個東方人,一個中國人,我想找到一種中國的材料,作為當代藝術的一個創作方向,用中國的方式來詮釋當代藝術,漆具有一種特有的代表性。我本次參展的作品《點石成金》中的有一些做成金石頭的作品,它們是用很傳統的脫胎工藝做成的,當然里面我沒有用麻布,而是用紙的方式來完成脫胎。觀眾看到的是一種表象,似乎看到了一塊金塊,實際上當你觸摸或者是拿起來的時候,會發現它非常輕,內里是紙做的、空心的。所以當觀眾看我的作品時,可能會被一種表像欺騙。這也正是我用這種材料、這種方式的一種隱喻,即表面金燦輝煌,但實際上并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但我也不僅僅用漆,同時還用了很多的材料,也會根據主題和現場來創作一些具有現場感的作品,這次參展的三組作品中,就有兩組是根據現場進行創作的。
雅昌藝術網:對于解讀您的作品,核心的點是什么?
沈也:人們總認為攝影是最真的.其實我們的眼睛是會受到欺騙的,攝影作品記錄下來的,也未必是正確的,那怕是瞬間記錄下來的東西,很多記錄都有可能有假像。很多東西都有一個內在和外在不同的可能性。
雅昌藝術網:是對日常經驗的懷疑嗎?這樣的話對觀眾來說,您的作品如果可以觸摸,是不是更能直觀地傳達您的理念。
沈也:我設了一個局,不想讓觀眾觸摸它,而是讓觀眾帶有一種懷疑的態度看來它,讓觀眾能夠有一種想象在里面。比如我本次參展的作品《金法》中的有一些做成金石頭的作品,它們是用很傳統的脫胎工藝做成的,當然里面我沒有用麻布,而是用紙的方式來完成脫胎。觀眾看到的是一種表象,似乎看到了一塊金塊,實際上當你觸摸或者是拿起來的時候,會發現它非常輕,內里是紙做的、空心的。所以當觀眾看我的作品時,可能會被一種表像……欺騙了。這也正是我用這種材料、這種方式的一種隱喻,即表面金燦輝煌,但實際上并不一定是那么回事。

沈也作品《點石成金》(局部)
對漆的借用,強調“去工藝”
雅昌藝術網:你用的是傳統的大漆嗎?
沈也:對,我只用傳統的大漆,這是一個底線,如果不是,就變成綜合材料了,跟大漆沒有關系。堅持只用大漆,對我的創作來說,反而是一個苛刻的要求,因為我需要用很純的大漆,來做一個跟漆工藝沒"關系"的作品。
雅昌藝術網:看得出來,您的作品并沒有刻意強調漆的工藝性。
雅昌藝術網:看得出來,您的作品并沒有刻意強調漆的工藝性。
沈也:漆這種材料在中國有特別悠長的歷史,原來說有五千年歷史,現在證實是有七千年的歷史。作為一位當代藝術家,關于漆藝,我其實是一個門外漢。雖然學習過一年漆工藝,但那也只是我對漆媒材的一種探討,我只想借用漆來呈現我的想法和觀念,并有意識地只用漆工藝中一、二種技法來創作。當再回到觀念的狀態時,觀眾就能看出我作品有自身的語徑。
雅昌藝術網:作為一位當代藝術家,您如何看待對于漆工藝性和當代性的探討?
沈也:漆確實有很強的工藝性在里面,我覺得作為一種傳統工藝,漆可以分成兩條路來走:該做工藝的做工藝,想借用這種方式的就大膽借用,像水墨畫既有繼續繼承傳統的方式畫魚、畫蝦的,也可以很當代。而且借用水墨的材料或借用漆的材料進行創作的方式,是中國特有的,中國的當代藝術家可以大有作為。
雅昌藝術網:對于漆這種材料,您的借用跟一般的漆藝家的創作最大的特點是對工藝的拋棄嗎?
沈也:我盡量從另外的一種方式來進行呈現漆,我的方式是“去工藝”。另外,大家知道漆這種材料是很貴的,我從另一種方式上來說其實是在消費漆。我沒有把它當成一種很昂貴的材料,比如有一些藝術家用寶石、金、銀來做作品,實際上也是一種對材料的消解。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創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