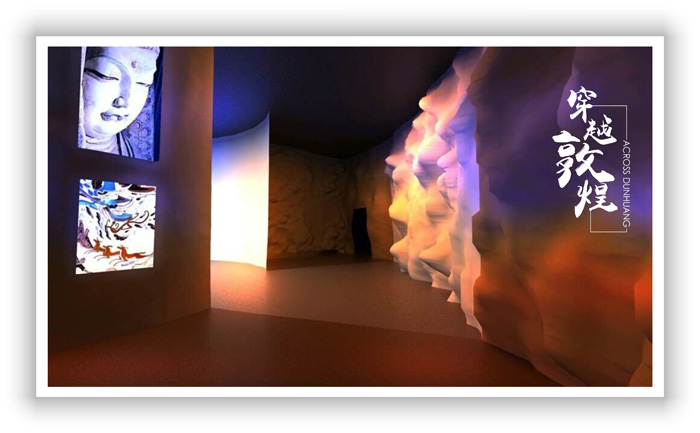意義的延伸與彌散
焦:簡單地說,作品的意義由兩部分構成。藝術家完成作品,只是完成了一半的事情;它必須和現場的展示效果,與觀眾的觀看發生關系后,另外一半才得以完成。
何 :這種觀念其實是現代主義雕塑與后現代主義雕塑分野時的一個重要的標志。現代主義認為,一件作品的意義只有藝術家才能賦予,作品的形式、結構原本就是一個自律的整體,從這個角度講,意義也是封閉的、完整的。后現代主義的藝術家并不這么看,他們強調,現場與觀眾都是作品意義的重要的組成部分,甚至觀看的時間、過程也能帶來意義。這樣一來,作品的意義就是開放的、向外彌散的。實際上,這些觀念主要是極少主義的藝術家在1967年前后提出的。但是,一旦這個觀念被后來的藝術家普遍接受之后,客觀上加速了雕塑向裝置藝術的轉變,或者說導致了“泛雕塑”現象的出現。回到《腳手架》這件作品,當觀眾進入展廳,發現有一件傳統意義上的雕塑,他們肯定會認為它是藝術品,但當發現是一個腳手架一樣的東西時,大部分人會把它看作是一個真實的腳手架,而不會認為是藝術品,更不會將它看作是一件雕塑。現場的視覺經驗與什么是雕塑的觀念最終會影響觀眾的判斷。
焦:這兩種經驗在那一刻完全融匯在了一起。這也是我長期思考的一個問題。有一段時間,朋友到我工作室參觀后就會問我,哪些是自己做的作品,哪些又不是?他們既好奇,又小心翼翼。2008年之前曾創作過一些放大了的包裝袋之類的作品,參觀的人一眼就覺得這是藝術品,但是此后的一些作品,同樣放在工作室里面,不過是跟整個工作室里的各種雜物堆在一起的,于是,他們產生了疑惑,不知道它們是不是藝術品?他們的這種感受影響了我,這是一個挺有意思的經驗,我想一直探索下去。后來就做了一個小《腳手架》,做完后就放在那里,也不能說是完成了。有一天,我找了一個木匠,讓他模仿我的作品再做一件和我的作品一樣的東西,他很認真的做了一個,但是這樣以來,作品的前后關系就發生了變化。另一個作品是一個木雕的箱子,我也希望討論箱子與它之間構成的關系。這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時間上的先后關系,還是現實與復制品之間的關系?這不得不讓我回到最初探索的起點,在新的場域條件下,翻制的東西能否重新融入現實,同時,它們與現實又形成怎樣的關系。
何 :杜尚在討論物品與藝術品關系時,用了一種“反藝術”和反藝術體制的方法,最終將藝術帶進了哲學領域。但是,當杜尚在觀念上解決了現成品在必要的條件下能成為藝術品之后,并沒有將作為藝術品的現成品重新融入到現實之中,即作品又如何與現場發生關系呢?事實上,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藝術家對“現場”也有不同的理解,“現場”自身的觀念也在發生變化。舉一個例子,當同一件作品放在不同的現場,意義有時就會完全不同。因此,在作品沒有變化的情況下,現場反而成為了一個變數。于是,什么樣的現場是藝術家需要的,或者說是作品意義生效最關鍵的因素呢?一般而言,現場可以分為這么幾種情況:一個是帶有普遍意義的日常化的現場,一個明確的具有社會屬性的現場,一個典型的美術館氛圍的現場,再有就是一個非常偶然化的現場。此前,你在“器空間”舉辦個展的時候,那個現場完全就是藝術化的,審美的層份比較多;但今年在“白盒子”的展覽上,這個現場則是一個非常日常化、生活化的。
焦:日常物品和現場怎樣發生關系的確需要藝術家去考慮。我的作品并不希望有一個很明顯的、很具體的現場,因為現場不具體反而會牽起很多的線索,帶來新的可能性,但是,也并不會因為線索過多反而會消解作品的意義,這需要藝術家自己的控制能力。
何:我覺得這個現場化的現實是具有社會學闡釋空間的。我發現,你作品中的一些現場大多是由一些非常具有生活化氣息的場景構成的,也是經常被人們所忽略的,換句話說,你通過現場化的呈現,喚起了我們對日常生活場景的再審視;另外就是這些場景與現場明顯具有某種社會屬性,它們大多是一些處于底層的、邊緣人群生活過的現場,因為,作品中有很強的生活痕跡在里面。所以,作為一個雕塑家,我認為既需要控制物理現場的能力,也需要探究場景背后蘊藏的社會學意義。此前我們談到物品、現場、觀眾所形成的劇場化的關系,而且,我個人認為,觀眾的觀看原本就是作品意義必要的組成部分。在此次白盒子的展覽中,你在布置現場的時候,實質已經預設了觀眾的觀看路線與觀看方式。
焦:沒有觀看的現場原本就沒有意義。另外一個就是,作品本身的呈現方式也能反映藝術家如何對生活進行思考。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