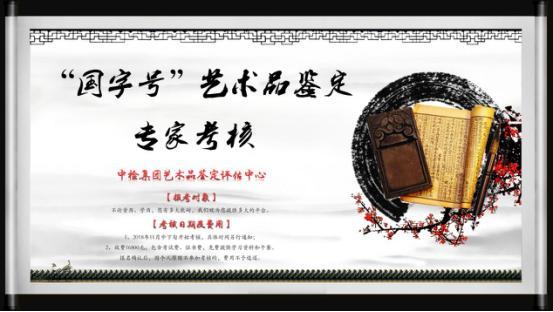書法家自抬潤格價背后的無奈
2015年的春拍又要登場,在佳士得、匡時這樣的大型拍賣會后面,隱藏的一些小型拍賣會不顯山露水,卻也有著自己的紅火市場。這些小型拍賣公司的業務不是成交藝術品,而是為藝術家做托兒,抬高藝術家的作品成交額,以此助書畫家提升潤格。
記者受邀參加一次藝術品拍賣,拍賣會的所見讓人瞠目結舌,書畫家拉上自己的親友充作競拍者,甚至自己也親自上陣,為自己的作品能拍得高價頻頻舉牌,感嘆之外皆是困惑。
但也儼然已經成了一些期待抬升書畫潤格的書畫家的有效途徑之一。潤格的上漲是由誰來決定的?利用拍賣會提升潤格為何蔚然成蔭?這種虛假的潤格提升方法有用嗎?能得到大眾的認可嗎?書畫家為自己賣力賺吆喝后尷尬的無奈是誰造成?
自賣自拍提升潤格
臨近拍賣會開場,稀稀拉拉的大廳椅子也只坐了一半。記者注意到前來到場的競拍者在開拍前,和參與拍賣的書畫藝術家很是熟稔,聊得火熱。
記者在拍賣會現場遇到了一位熟識的藝術家,原以為書法家親臨現場只是想看看自己的書法作品的行情如何,記者卻注意到這個書法家也坐到席位上,手上也拿了個號碼牌。
記者事后從拍賣公司了解情況時,拍賣公司的工作人員也不避諱,直言現在市場情況就是這樣,像他們這種小的拍賣會,最重要不是成交量、成交金額是多少。主要是為書畫家做托,抬高作品潤格,以便確定新一年的自己的作品價格。
書畫潤格在古代也都是由書畫家和市場自行約定俗成,至今也沒有一個完全由國家主導的機構,民間書畫潤格評定機構多如牛毛,監管機制的缺失也讓書畫評定機構隨意而為,有效、公正性成了走過場,竟也到了交上千塊評定費能免費發一個潤格證書的程度。
潤格的多少對沒有明確規定,但是國家級會員,你的潤格可以喊多少,省級會員,你的潤格可以喊多少,都大體上有個規矩:如果你有點職務,主席、理事什么的,可以往上浮動一點。即使有這樣的不成文的規定,書畫家仍舊每年為自己的潤格往上調,書畫作品作為商品,沒有明確的價值界定,自然監管也就更談不上,潤格多少大致也由畫家自己“拍板”。拍賣會上作品最后的落錘價往往成了書畫家正大光明的漲價砝碼,拍賣的作品落錘價除以作品尺幅,就是新一輪的潤格了。
抬上去的價格也就是個數字
即使是不懂行的人,也知道書畫界有這樣一句話,“好字不如爛畫”,究其原因,記者曾經采訪過業內專家,受大眾的傳統認知所限,總以為畫畫費工夫,毛筆字就短短一分鐘就可完成,費工夫等于用心,用心等于畫得好,而毛筆字在時間上可謂是失了先聲。
一些書法家為提升潤格費勁心力,像記者見過的這位,親戚都拉來助陣,只為以后再宣傳推廣自己時,能有個賣點,證明自己潤格提升是有真實依據的,是市場的真是行情,而非自己自行定價,對于外行人,很難看出其中不為人知的一面。
相較之下,古人的潤格叫賣可謂是風雅至極,鄭板橋晚年時不堪求畫人的煩擾,公然寫出了自己的潤格,謂之《板橋潤格》: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條幅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為賴賬。年老體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任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
言語雖然直白卻也超凡脫俗,晚年時的鄭板橋畫竹已頗受大家青睞,他的書畫潤格放在當今的書畫圈也就是個白菜價。古代白銀的購買力大致是一兩白銀等于一千元人民幣,也就是說鄭板橋當時賣畫是大幅作品6000塊,扇子500塊。
相較于鄭板橋的“實在”,現在的書畫家的潤格賣起來那叫一個不含糊,張嘴就是一平方尺20000塊,一幅大尺寸作品動輒標價十萬。
一位畫花鳥的中國美協會員,在他的宣傳冊上赫然印著美術作品潤格20000-30000元/平方尺。一位畫仕女圖的畫家張口就是一幅畫十萬,記者在查閱了他的簡歷后,不是中國美協會員,也不是省美協會員,甚至也只是半路出家的畫家。其中的水分不言而喻,卻也形成了一個書畫圈特有的現象,不怕作品叫價高,就怕潤格低了顯不出自己的身份。
當然賣不賣的出去另當別論,聲勢得先造起來,也是一些書畫家的無奈之舉,曾有位畫家吐苦水,“不漲不行,即使賣的低也得讓潤格的數字好看,否則給前來收藏作品的人來說,會覺得名氣不大,所以潤格才這樣低。潤格高了可以打折,也能滿足一些藏家喜好還價的心理。”
市場環境良莠不齊
書畫的裝飾、教育、收藏、禮品功能讓大眾也開始了這方面的消費。藝術家一批一批的涌出來,在大眾還沒有做好了解這個市場的準備時,書畫家已經以上位者的姿態為這個行業定規矩了。
以為藝術家想要走到人前,除了自身作品的藝術性,背后其實考驗的其實是市場資本的運作。從宣傳到畫展再到拍賣,其實遵循了藝術家被市場認可的先行必要條件,現實是,沒有多少畫家有這樣專業的團隊來運營操作。
更多的書畫家其實自己為自己充當經紀人,在創作作品的同時,為自己謀出路,雖然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但在藝術領域里,書畫家精力過多的被這些“俗事”分開了。
其中雇不起經紀人來打理自己的藝術品是一回事,還有更多的書畫家的藝術性并不足以進入知名經紀人、專業畫廊、大型拍賣機構的法眼。但是市場如此之大,也并不是王羲之、蘇軾、黃公望這些古代“大能”壟斷的,也不是曾梵志這些當代藝術家能占全的,更多的平民收藏市場被拓展開,市民收藏也出不起那樣的高價。
姑且可以說這些藝術水準一般的書畫家市場還是很大的,但是“清高”的格調讓他們拉不下臉來,把自己的書畫作品當作一般性的藝術商品出售,一方面面臨作品賣不出去的尷尬,另一方面把自己的作品潤格逐年抬升以期自己的作品是價值很高的藝術品的高姿態。這兩者其實是相悖的,但現在市場的情況是實際只能賣1000的作品一定要標到幾萬,否標出幾百的作品怎么對得起自己藝術家的稱號。也足以說明了市場上辨識藝術品的價值是以標價高低來論的膚淺論調,但也符合普通沒有藝術欣賞能力的大眾,藝術家也就隨波逐流了,堅決只標高價,否則就是掉價。
作品標出越來越高的潤格是如何來的?需要給大眾一個看似權威的交代,所以自拍自賣的這種方式變屢見不鮮,屢用不爽了。更遑論那些出售潤格證書的看似名頭很大的認證機構了。
藝術家的心態要調整,市場的監管要跟上,普通收藏愛好者的鑒賞能力要提升,這都是藝術走向大眾消費需要考量的。(編輯/麥穗兒)